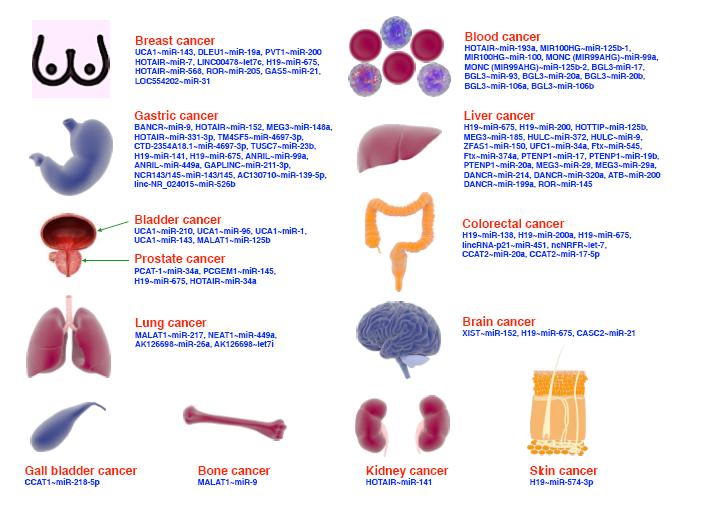在過去的20年里,保留瓣膜的主動脈根部置換術(Valve sparing aortic root replacement,VSARR)已經成為治療主動脈根部動脈瘤患者的一種成熟手術。VSARR能保留主動脈竇部的幾何結構和患者的主動脈瓣,具備良好的血流動力學,避免了人工瓣膜和終身抗凝[1–3]。然而,在治療先天性心臟病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擴張的患者時,VSARR的作用仍不確定。目前有研究報道了法洛四聯癥(tetralogy of Fallot,TOF)術后出現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接受VSARR手術治療的經驗,但局限于報道的病例數,其中遠期效果仍存有爭議,且這類患者的手術指征尚無統一的共識[4–8]。我們回顧性分析對于TOF術后出現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的患者采用VSARR手術治療的中期效果,為此類患者的手術方式提供選擇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我院2016—2022年我院TOF術后合并主動脈根部擴張患者采用VSARR治療的患者。根據納入標志:TOF術后主動脈根部擴張患者采用VSARR手術治療的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主動脈瓣感染、風濕等病變導致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患者;(2)結締組織病及大動脈炎等其他原因導致升主動脈及主動脈竇部擴張患者;(3)未行解剖根治TOF合并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或升主動脈擴張的患者;(4)同期行主動脈瓣置換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心臟CT檢查并明確診斷。
1.2 手術方法
常規采用胸骨正中切口,經升主動脈遠端-上下腔靜脈插管建立體外循環,右上肺靜脈插管,行左心引流、減壓。采用中度低溫28~32℃,并經主動脈根部或冠狀動脈開口順行性灌注心臟停搏液,部分患者聯合冠狀靜脈竇逆行灌注。將主動脈切開至主動脈竇口上方,使用測瓣器確定竇口交界處的直徑,仔細評估主動脈根部解及保留瓣膜可行性,包括瓣環內徑、冠狀動脈開口位置、瓣葉質量、幾何學高度(geometry height,gH)和有效高度(effective height,eH)。
1.2.1 再植(David)技術
切除擴張的竇,保留約5 mm的主動脈管壁,游離主動脈根部至瓣環水平,并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修剪成“紐扣”狀。選擇直徑不同的2根人工直血管。6~12針2-0 縫線帶墊片自主動脈瓣環由內向外間斷褥式縫合,將主動脈瓣及剩余瓣竇組織套入直徑較大的直血管內,縫線穿過人工血管,打結固定并環縮主動脈 瓣環至目標內徑(主動脈瓣口內置合適大小的 Hegar探條)。4-0 Prolene間斷褥式縫合,將瓣葉交界最高點固定于人工血管的竇管交界水平,然后5-0 Prolene連續縫合,將瓣葉附著緣周圍管壁固定于人工血管內。接著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分別移植于左右瓣竇內相應位置。最后,取直徑與主動脈瓣環直徑匹配的人工血管,在竇管交界水平與前述人工血管端端吻合,置換升主動脈(圖1a)。
1.2.2 重塑(Yacoub)技術
通過游離主動脈根部,6針2-0縫線帶墊片自主動脈瓣環平面由內向外間斷褥式縫合,裁剪寬約5 mm的人工血管環,將其套在主動脈瓣環水平,縫線穿過血管環,在瓣口內置目標直徑的Hegar探條,然后打結固定,將Hegar探條取出,此時的瓣環內徑即是目標直徑。把Valsalva人工血管的竇部裁剪成三葉舌狀(在二葉主動脈瓣病例中,裁剪成相應的二葉舌狀),置換主動脈竇部,最后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移植于相應的竇部(圖1b)。
1.2.3 弗羅里達袖(Florida sleeve)技術
將主動脈根部游離至瓣環以下水平,人工血管套入主動脈根部進行加固,分別保留左、右冠狀動脈,將主動脈近段與人工血管連續縫合后,再與主動脈遠端吻合,重建生主動脈[9](圖1c)。
所有患者都在出手術室之前用經食管超聲心動圖(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仔細評估瓣膜的功能。術后給予阿司匹林5 mg/kg,低強度抗凝治療6個月。術后3個月、6個月和1年常規隨訪,此后每年復查1次。隨訪內容包括復查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胸部X線片。臨床隨訪數據包括包括需要新主動脈擴張、左室流出道狹窄、瓣膜反流、對主動脈根部進行再次手術、出血、血栓栓子事件和后續需再次行心血管干預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5.0 分析軟件分析數據。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對于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2 結果
共納入14例患者,其中男8例、女6例,接受手術時的中位年齡22(12~48)歲,中位體重45.5(30.0~62.5)kg。主動脈瓣重度反流5例,中度反流4例,主動脈輕度及以下反流5例。主動脈竇部擴張6例,升主動脈明顯擴張8例,同期合并室間隔缺損殘余分流1例,合并重度肺動脈瓣反流9例。心臟超聲測量平均主動脈瓣環直徑24(22~35mm),竇部平均直徑39(22~55)mm,升主動脈平均直徑35(39~59)mm, 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55%±6.2%。心電圖均提示不同程度左心室肥厚。VSARR的手術方式為David手術10例,Yacoub手術2例,Florida sleeve 2例。全組無手術死亡。14例患者使用直血管,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124± 30.0)min,總體外循環時間(206.0±22.5)min。14例患者術后平均機械輔助通氣時間(14.2±12.5)h,平均監護室停留時間(3.5±1.3)d。術后患者平均隨訪時間2.9(0.4~6)年,1例患者出現輕度主動脈瓣反流,其余患者均為微量或無主動脈瓣反流,1例患者出現左室流出道輕度狹窄,余所有患者左室流出道未見明顯狹窄,新主動脈無明顯擴張,無明顯瓣膜反流,無再次手術干預。
3 討論
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是TOF術后發生主動脈瓣反流的主要原因,其可能與主動脈根部的生長與TOF修復后的體表生長不相稱相關,或者手術修復后血流的正常化,潛在的主動脈病變導致進行性的主動脈根部擴張,如主動脈瓣二葉式畸形、馬凡綜合征[6,10-11]。VSARR手術因其能保留主動脈瓣以及竇狀幾何結構,改善血流動力學和不必終身抗凝的治療的優點,已成為治療主動脈根部動脈瘤患者的主要手術方式之一[1,12-13]。然而,在接受過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如肺動脈閉鎖矯治、TOF矯治、大動脈轉位矯治等)的患者,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擴張,再次行VSARR手術的效果仍不確定。Baliulis等[4]報道了11例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平均年齡(30.5±7.7)歲]因主動脈根部進行性擴張而行VSARR術,術后10例患者術后主動脈瓣功能滿意,表明對之前手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逐漸擴張的成年先天性患者,可以安全地進行VSARR手術。Eishi等[14]的研究表明TOF術后,對于環狀或竇管交界處擴張而沒有明顯的Valsalva竇擴張而出現主動脈反流的患者來說,VSARR手術可能是一個可取的選擇。在本組患者中全組無手術死亡,術后1例患者出現輕度主動脈瓣反流,其余患者均為微量或無主動脈瓣反流,1例患者出現左室流出道輕度狹窄,余所有患者左室流出道未見明顯狹窄,顯示對于低齡兒童或者成人,VSARR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手術治療方式,但對于年齡偏小的兒童,尚缺乏臨床經驗。Patel等[15-16]報道在兒童中應用VSARR的短期和中期經驗。在這些研究中,研究的早期結果是良好的,表明了兒童再植技術在存活率、術后環狀擴張和避免主動脈瓣反流方面的優越性。Fraser等[17]的研究顯示,對于患有主動脈根部擴張的兒童來說,保留瓣膜的根部置換術是一個安全而有效的選擇,但需對主動脈瓣的狀態進行評估,如存有明顯的瓣膜不規則、或廣泛鈣化、嚴重脫垂和多裂缺的主動脈瓣的患者不適宜行VSARR手術。
VSARR手術的運用于先天性心臟病患者的挑戰在于先天性和手術術后心臟解剖的特殊結構。例如主動脈根部在先天性病變患者中可能有一個非常水平的位置,與它在水平面35°~45°的正常位置相反,這使得觀察主動脈瓣變得相當困難,并影響到在手術過程中保持主動脈瓣正確幾何形狀的效果。此外,當合并其他需手術處理的心臟解剖畸形是,會延遲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增加了一定的手術風險[5]。Kari等[18]的多中心研究也顯示,對于主動脈瓣/根部不對稱、嚴重主動脈瓣反流、左心室射血分數偏低和主動脈瓣二葉式畸形的患者,行主動脈瓣置換要優于VSARR手術。本組病例患者均接受了VSARR手術治療,且中期隨訪表明治療結果滿意,但納入的樣本量相對不多,未納入主動脈瓣置換的患者,今后需要開展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來評估比較VSARR手術與主動脈瓣置換在TOF術后主動脈擴張中的治療效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希負責數據收集及初稿撰寫;譚今負責文獻檢索;于濤負責隨訪數據收集;黃克力負責審閱手術方法;蔣露負責全文審校。
在過去的20年里,保留瓣膜的主動脈根部置換術(Valve sparing aortic root replacement,VSARR)已經成為治療主動脈根部動脈瘤患者的一種成熟手術。VSARR能保留主動脈竇部的幾何結構和患者的主動脈瓣,具備良好的血流動力學,避免了人工瓣膜和終身抗凝[1–3]。然而,在治療先天性心臟病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擴張的患者時,VSARR的作用仍不確定。目前有研究報道了法洛四聯癥(tetralogy of Fallot,TOF)術后出現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接受VSARR手術治療的經驗,但局限于報道的病例數,其中遠期效果仍存有爭議,且這類患者的手術指征尚無統一的共識[4–8]。我們回顧性分析對于TOF術后出現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的患者采用VSARR手術治療的中期效果,為此類患者的手術方式提供選擇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我院2016—2022年我院TOF術后合并主動脈根部擴張患者采用VSARR治療的患者。根據納入標志:TOF術后主動脈根部擴張患者采用VSARR手術治療的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主動脈瓣感染、風濕等病變導致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患者;(2)結締組織病及大動脈炎等其他原因導致升主動脈及主動脈竇部擴張患者;(3)未行解剖根治TOF合并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或升主動脈擴張的患者;(4)同期行主動脈瓣置換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心臟CT檢查并明確診斷。
1.2 手術方法
常規采用胸骨正中切口,經升主動脈遠端-上下腔靜脈插管建立體外循環,右上肺靜脈插管,行左心引流、減壓。采用中度低溫28~32℃,并經主動脈根部或冠狀動脈開口順行性灌注心臟停搏液,部分患者聯合冠狀靜脈竇逆行灌注。將主動脈切開至主動脈竇口上方,使用測瓣器確定竇口交界處的直徑,仔細評估主動脈根部解及保留瓣膜可行性,包括瓣環內徑、冠狀動脈開口位置、瓣葉質量、幾何學高度(geometry height,gH)和有效高度(effective height,eH)。
1.2.1 再植(David)技術
切除擴張的竇,保留約5 mm的主動脈管壁,游離主動脈根部至瓣環水平,并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修剪成“紐扣”狀。選擇直徑不同的2根人工直血管。6~12針2-0 縫線帶墊片自主動脈瓣環由內向外間斷褥式縫合,將主動脈瓣及剩余瓣竇組織套入直徑較大的直血管內,縫線穿過人工血管,打結固定并環縮主動脈 瓣環至目標內徑(主動脈瓣口內置合適大小的 Hegar探條)。4-0 Prolene間斷褥式縫合,將瓣葉交界最高點固定于人工血管的竇管交界水平,然后5-0 Prolene連續縫合,將瓣葉附著緣周圍管壁固定于人工血管內。接著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分別移植于左右瓣竇內相應位置。最后,取直徑與主動脈瓣環直徑匹配的人工血管,在竇管交界水平與前述人工血管端端吻合,置換升主動脈(圖1a)。
1.2.2 重塑(Yacoub)技術
通過游離主動脈根部,6針2-0縫線帶墊片自主動脈瓣環平面由內向外間斷褥式縫合,裁剪寬約5 mm的人工血管環,將其套在主動脈瓣環水平,縫線穿過血管環,在瓣口內置目標直徑的Hegar探條,然后打結固定,將Hegar探條取出,此時的瓣環內徑即是目標直徑。把Valsalva人工血管的竇部裁剪成三葉舌狀(在二葉主動脈瓣病例中,裁剪成相應的二葉舌狀),置換主動脈竇部,最后將左右冠狀動脈開口移植于相應的竇部(圖1b)。
1.2.3 弗羅里達袖(Florida sleeve)技術
將主動脈根部游離至瓣環以下水平,人工血管套入主動脈根部進行加固,分別保留左、右冠狀動脈,將主動脈近段與人工血管連續縫合后,再與主動脈遠端吻合,重建生主動脈[9](圖1c)。
所有患者都在出手術室之前用經食管超聲心動圖(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仔細評估瓣膜的功能。術后給予阿司匹林5 mg/kg,低強度抗凝治療6個月。術后3個月、6個月和1年常規隨訪,此后每年復查1次。隨訪內容包括復查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胸部X線片。臨床隨訪數據包括包括需要新主動脈擴張、左室流出道狹窄、瓣膜反流、對主動脈根部進行再次手術、出血、血栓栓子事件和后續需再次行心血管干預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5.0 分析軟件分析數據。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對于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2 結果
共納入14例患者,其中男8例、女6例,接受手術時的中位年齡22(12~48)歲,中位體重45.5(30.0~62.5)kg。主動脈瓣重度反流5例,中度反流4例,主動脈輕度及以下反流5例。主動脈竇部擴張6例,升主動脈明顯擴張8例,同期合并室間隔缺損殘余分流1例,合并重度肺動脈瓣反流9例。心臟超聲測量平均主動脈瓣環直徑24(22~35mm),竇部平均直徑39(22~55)mm,升主動脈平均直徑35(39~59)mm, 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55%±6.2%。心電圖均提示不同程度左心室肥厚。VSARR的手術方式為David手術10例,Yacoub手術2例,Florida sleeve 2例。全組無手術死亡。14例患者使用直血管,平均主動脈阻斷時間(124± 30.0)min,總體外循環時間(206.0±22.5)min。14例患者術后平均機械輔助通氣時間(14.2±12.5)h,平均監護室停留時間(3.5±1.3)d。術后患者平均隨訪時間2.9(0.4~6)年,1例患者出現輕度主動脈瓣反流,其余患者均為微量或無主動脈瓣反流,1例患者出現左室流出道輕度狹窄,余所有患者左室流出道未見明顯狹窄,新主動脈無明顯擴張,無明顯瓣膜反流,無再次手術干預。
3 討論
進行性主動脈根部擴張是TOF術后發生主動脈瓣反流的主要原因,其可能與主動脈根部的生長與TOF修復后的體表生長不相稱相關,或者手術修復后血流的正常化,潛在的主動脈病變導致進行性的主動脈根部擴張,如主動脈瓣二葉式畸形、馬凡綜合征[6,10-11]。VSARR手術因其能保留主動脈瓣以及竇狀幾何結構,改善血流動力學和不必終身抗凝的治療的優點,已成為治療主動脈根部動脈瘤患者的主要手術方式之一[1,12-13]。然而,在接受過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如肺動脈閉鎖矯治、TOF矯治、大動脈轉位矯治等)的患者,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擴張,再次行VSARR手術的效果仍不確定。Baliulis等[4]報道了11例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平均年齡(30.5±7.7)歲]因主動脈根部進行性擴張而行VSARR術,術后10例患者術后主動脈瓣功能滿意,表明對之前手術后出現主動脈根部逐漸擴張的成年先天性患者,可以安全地進行VSARR手術。Eishi等[14]的研究表明TOF術后,對于環狀或竇管交界處擴張而沒有明顯的Valsalva竇擴張而出現主動脈反流的患者來說,VSARR手術可能是一個可取的選擇。在本組患者中全組無手術死亡,術后1例患者出現輕度主動脈瓣反流,其余患者均為微量或無主動脈瓣反流,1例患者出現左室流出道輕度狹窄,余所有患者左室流出道未見明顯狹窄,顯示對于低齡兒童或者成人,VSARR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手術治療方式,但對于年齡偏小的兒童,尚缺乏臨床經驗。Patel等[15-16]報道在兒童中應用VSARR的短期和中期經驗。在這些研究中,研究的早期結果是良好的,表明了兒童再植技術在存活率、術后環狀擴張和避免主動脈瓣反流方面的優越性。Fraser等[17]的研究顯示,對于患有主動脈根部擴張的兒童來說,保留瓣膜的根部置換術是一個安全而有效的選擇,但需對主動脈瓣的狀態進行評估,如存有明顯的瓣膜不規則、或廣泛鈣化、嚴重脫垂和多裂缺的主動脈瓣的患者不適宜行VSARR手術。
VSARR手術的運用于先天性心臟病患者的挑戰在于先天性和手術術后心臟解剖的特殊結構。例如主動脈根部在先天性病變患者中可能有一個非常水平的位置,與它在水平面35°~45°的正常位置相反,這使得觀察主動脈瓣變得相當困難,并影響到在手術過程中保持主動脈瓣正確幾何形狀的效果。此外,當合并其他需手術處理的心臟解剖畸形是,會延遲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增加了一定的手術風險[5]。Kari等[18]的多中心研究也顯示,對于主動脈瓣/根部不對稱、嚴重主動脈瓣反流、左心室射血分數偏低和主動脈瓣二葉式畸形的患者,行主動脈瓣置換要優于VSARR手術。本組病例患者均接受了VSARR手術治療,且中期隨訪表明治療結果滿意,但納入的樣本量相對不多,未納入主動脈瓣置換的患者,今后需要開展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來評估比較VSARR手術與主動脈瓣置換在TOF術后主動脈擴張中的治療效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希負責數據收集及初稿撰寫;譚今負責文獻檢索;于濤負責隨訪數據收集;黃克力負責審閱手術方法;蔣露負責全文審校。